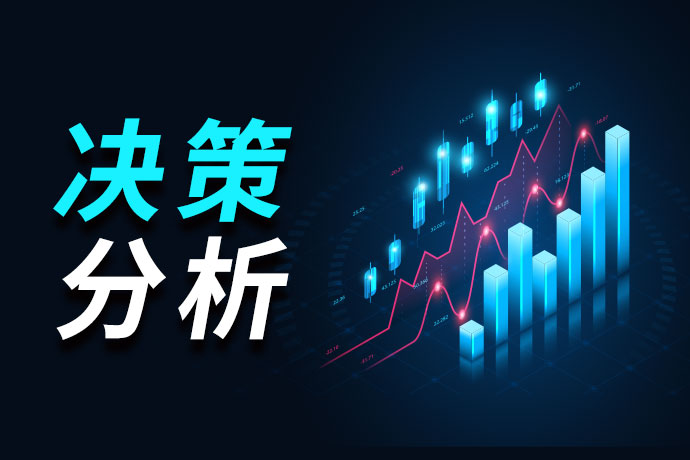本文刊发于华盛顿邮报,作者乔治·F·威尔自1974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开设专栏,并于1977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

西方迫切需要重新界定“西方”这一概念。否则,西方既无法理解自身,也无法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如果乌克兰要避免被肢解、保持国家地位不被削弱,就必须以亨廷顿的框架来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与利害。
亨廷顿(1927—2008)有时判断失误。1993年,他曾写道:“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应当很低。他们同属斯拉夫民族,主要信奉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关系密切。”
他也未能预见到西方的强大吸引力,正将乌克兰从普京试图强加的文明体系中拉扯出来。
然而,在冷战结束后那段乐观情绪高涨的时期,亨廷顿却保持了清醒。他主张,西方所代表的个人主义、人权宪法保障、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会成为这个星球的“普世文明”。
由于这些价值观无法普遍适用,西方注定要与其他文明共存,有时甚至发生冲突。亨廷顿曾警告说,不要在苏联解体后沉溺于自我陶醉的胜利情绪。他表示:“文明之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如今,这一预言再次显现。
在新书《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中,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学者乔治奥斯·瓦鲁夏基斯指出,“从柏拉图到北约”的直线式叙述是一种严重简化。最初,人们相信“向阳神话”——文明的进步如同太阳般由东向西推进。
尽管从罗马帝国到基督教世界(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都存在东西分歧,但在近几个世纪中,“西方”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核心是欧洲及其大西洋彼岸的延伸。
在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浪潮中,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痛斥一种“异于西方文明”的思想:“个体的安全、幸福与荣耀,要通过屈服于群众情绪的强制与全能国家的统治才能获得。”
如今,普京的宣传国家操纵群众情绪,习近平的监控国家全面掌控个体,这些现象应当促使西方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
1945年以前,关于“西方”的界定曾多次变化,有时并不包括德国。德国在1990年统一十年后,一部畅销历史书以《德国:通往西方的漫长道路》为题。1945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因战时情感作祟,人们一度忽略了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条约,短暂地把俄罗斯视为西方的一部分。
俄罗斯往往被视为西方的“他者”,甚至是最典型的“他者”。正是通过与俄罗斯的对比,西方才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文明共同体”,瓦鲁夏基斯如此指出。为了加强与欧洲的文化纽带,哈佛大学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著名的“国际研讨班”,发起人之一就是年轻的欧洲移民亨利·基辛格。
亨廷顿指出,西方注定要与其他强大且有主张的文明共处,这种共处可能是危险的。而在今天的文明冲突中,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互不理解”并非对等。
普京理解西方,并且出于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思维而鄙视它。他否定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传统,也拒绝雷蒙·阿隆的理想——“真正的‘西方人’,唯一毫无保留接受的,是他拥有批评自己文明的自由,以及改善它的机会。”
普京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浸入式的族群-宗教认同论,这一信仰与西方注定处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中。
特朗普之所以对普京不愿像地产商一样理性地各退一步感到困惑,是因为他缺乏想象力。他无法理解普京如何看待自己,这是他对深层、持久的文明冲突缺乏认知的表现。
瓦鲁夏基斯援引美国学者詹姆斯·柯斯与迈克尔·金梅奇的话指出,“没有哪位近代美国总统像特朗普那样,更准备退出西方文明与西方这个共同体。”
他还表示,“说特朗普在2017到2021年任期内是美国首位非西方总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不过,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波兰发表演讲时曾十次提到“西方”。他说,波兰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西方的防卫最终依靠的,不仅是手段,更是其人民取胜的意志。”
因此,特朗普当时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求生的意志。”
然而,人们仍然质疑,他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提过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