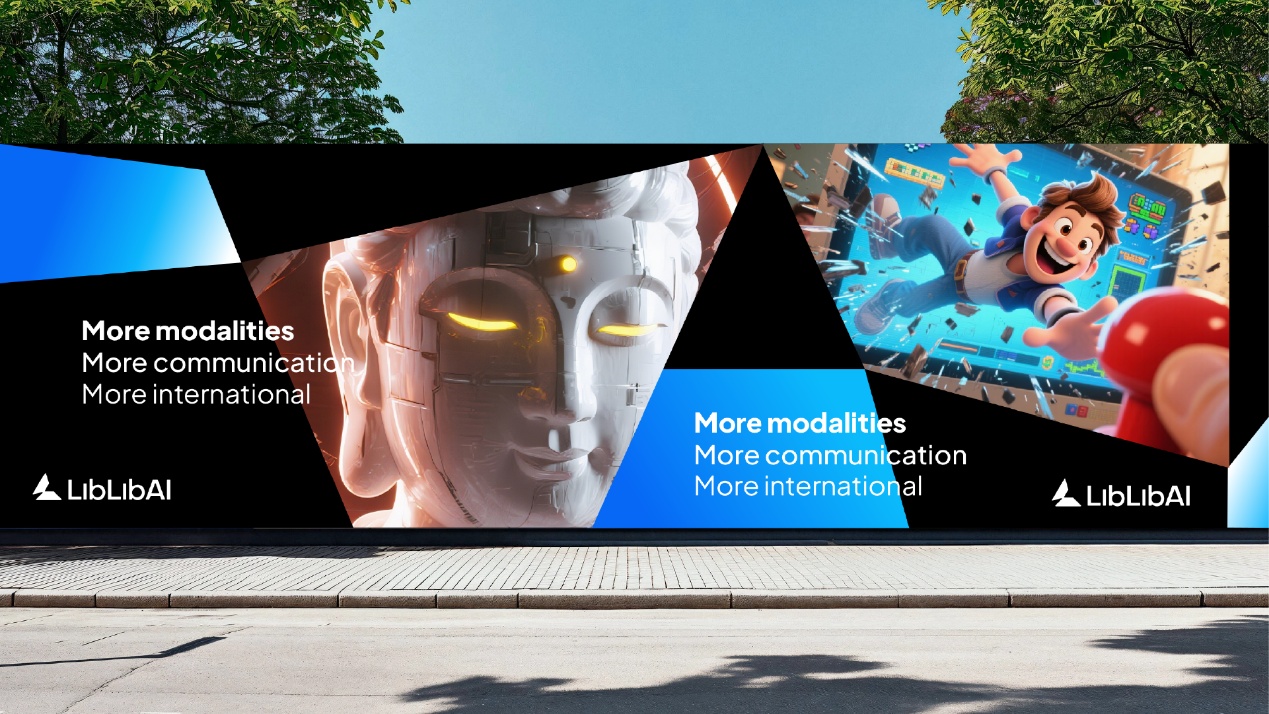本文刊发于经济学人,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当中国领导人谈论经济时,经常使用共产党的术语,比如“双循环”“新质生产力”“内卷”等。
最近的官方评论中,还出现了一个源自主流经济学的术语:“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
去年,习近平表示,TFP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标志”。10月21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呼吁中国“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种表述鼓舞人心。但中国真正要争取的这个“奖项”到底是什么?
TFP最好的定义方式,或许是说“不是什么”: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来源于调动更多劳动力,并为其配备更多机器和基础设施。而TFP增长则涵盖了除去这些投入因素外的所有其他部分。
这是经济学家用来描述那些无法通过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增加来解释的产出增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诺德·哈伯格曾说,提高TFP的方式“至少有1001种”。他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一家服装厂的老板通过在车间播放背景音乐,使缝纫工的产出提高了20%。
TFP通常与技术和效率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努力或支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形容这是“灵感”,而不是“汗水”。
本周召开的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审议了新的五年规划,希望国家的发展更依靠“灵感”而不是“汗水”。
他们别无选择。未来,中国无法再依赖新增劳动力:自2016年以来,劳动力数量已减少超过2000万。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中国也难以维持过去那种快速的资本积累速度。
当中国领导人重新构想经济增长模式时,TFP成为他们衡量成效的重要标尺。
不过,中国很少公布官方的TFP增长数据。目前最多引用的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世界数据表”(Penn World Table),这一项目最初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创建,如今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伯特·芬斯特拉、格罗宁根大学的罗伯特·英克拉尔和马塞尔·蒂默负责。
项目通过统一价格体系,计算出全球可比的GDP与生产要素数据。据估算,全球三分之二的增长研究,都引用了这项数据。
最近发布的版本显示,中国的增长乏善可陈。2021年发布的第十版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的TFP实际上是下降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投入增加所预期的水平。在118个有数据的国家中,中国TFP增长排名第83。
这样的数据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哈尔·布兰兹和塔夫茨大学的迈克尔·贝克利合著的《危险地带》一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估算。
他们创造了“峰值中国”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正陷入类似苏联的“泥潭”。
但本月发布的最新一版“宾夕法尼亚世界数据表”却描绘出不同的图景。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到2019年的TFP年均增长2.3%,在全球排名第六。以2013年至2023年为周期的近十年中,中国的TFP增长排名第三。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
TFP的表现取决于GDP增长与投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尽管中国投入增长基本未变,但新版本选择了不同的GDP计算方式,采用了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而早期版本使用的是北京大学的伍晓鹰所估算的数据。由于中国官方数据中的增长率高于伍晓鹰的估算,中国的TFP数据因此也显得更亮眼。
这一转变的背后,有多个考虑。英克拉尔表示,偏离官方更熟悉的数据可能会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
“如果我们做太多这样的调整,人们就不再使用这个数据库了,因为他们无法把这些数字与其他来源对照起来。”他说。
英克拉尔也不愿专门对中国进行特别处理。确实,中国的数据曾引发质疑,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数据也有类似问题。
英克拉尔还指出,伍晓鹰早年设定的一些假设,如今不一定仍然合理。在估算工业增长时,伍晓鹰会从上百种商品的实物产量入手,比如煤的吨数、白酒的升数、布料的米数。他将这些增长率结合成一个指数,并进行加权,以反映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对教育、金融、政府、医疗等服务行业,伍晓鹰采用更简单的方法,假设其人均产出不变,即每年增长为0%。
这与官方数据中5%到6%的增长率存在明显差距。
伍晓鹰的方法,为官方数据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但随着中国工业越来越复杂,产出已经难以用实物数量准确衡量。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日益上升,因此他假设服务业人均产出不变的前提变得更加关键。
虽然这样的假设符合许多国家的普遍情况,但也有例外。英克拉尔指出,至少有七个经济体(包括印度和马来西亚),服务业的人均产出增长超过了2%。
如果有人最清楚中国数据是否真实可信,那无疑是中国领导层。如果他们对官方数据有信心,那就可以为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感到满意。如果他们私下认为伍晓鹰的数据更接近现实,那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提高TFP的方式有1001种,中国领导人或许应该从改善统计数据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