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彭博网站,作者米沙尔·侯赛因是彭博社《周末版》的特约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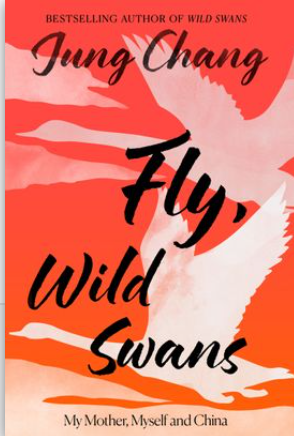
在1991年出版《鸿》时,张戎开创先河,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而获得全球声誉,书的副标题是《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部深具个人色彩的作品,描绘了她的祖母、母亲和她本人所经历的极端时代,从缠足到饥荒,从共产党清洗到劳改营。
读者通过这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产生了情感共鸣。此后,张戎又出版了其他著作,包括与丈夫合著的2005年毛泽东传记,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张戎似乎拥有了一切——中国开放带来的机遇,伦敦的自由生活,以及与家人往返的便利。1993年,她曾表示自己很有信心,中国的经济繁荣是未来实现民主的最大保障。
如今,她的想法已大不相同。她重返家族故事,推出新作《飞吧,鸿》(哈珀柯林斯出版社,9月16日出版),延续《鸿》的结尾,从1978年讲起,但新书充满痛楚——因为张戎说,她已经无法回到中国。
以下是经过删节与整理的采访内容。

时隔三十多年,再次出版以《鸿》为标题的书,有什么感受?
写这本续集让我非常激动。很多年来,不断有人催我写这本书。我总觉得时机不成熟,也没有足够的内容。现在我觉得时机到了,我可以更新我家族的故事,也更新中国的故事。
我的人生和中国历史紧密相连。《鸿》结尾定格在1978年,那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了。
我成为最早一批走出中国、来到西方的人之一。如今,快五十年过去了,中国又走到另一个转折点。习近平决意将中国带回毛时代,并把西方视为对手,甚至是敌人。
说中国正在被带回毛时代,这画面非常强烈。你亲眼见过那个时代的贫困、强迫劳动和野蛮压迫。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那些可怕的事情,在一些人眼中——坚定的共产党人、毛派、斯大林主义者,比如习近平——其实并不可怕。我认为,有些人至今还在怀念那个时代。
共产主义的捍卫者常说,“要做蛋卷,总得打碎鸡蛋。”
在他们看来,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做这些事是合理的。
我们稍后会谈到你眼中的当代中国,以及世界的变化。但我想先回到书中关于家庭的部分,你1950和60年代在成都的童年。你的父母在共产党刚掌权时,是忠诚的信徒,对吗?
是的。我母亲其实有些保留态度,但他们俩都是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他们痛恨当时社会的不公,我母亲尤其憎恨纳妾制度。
我外祖母就是妾,吃了很多苦。我母亲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而共产党承诺要解放女性。
但共产党有个特点,一旦加入就没有退出的可能。
退出——就像我母亲在早期曾想的那样——会被视为叛党,并受到相应的惩罚。一旦被迫留下,就只能尽量往好处想。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早期会找各种理由,为那些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事情辩解。
但“大饥荒”成了转折点。1958年至1961年之间,大约有四千万人因饥饿而死。这个数字极其惊人。你父母当时虽然不可能知道具体数字,但他们肯定看到了影响吧?
他们不会知道饥荒的规模,普通人基本都不知道。很多人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为了写毛的传记,我和我丈夫——也是合著者——乔恩·哈利迪做了大量研究,才得出这个数字。
我父母并不知道饥荒的具体原因,但他们知道,是他们的政党造成了这场灾难。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也实际上是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转折点。
这场饥荒的根源,是1958年开始的所谓“大跃进”五年计划,意在快速工业化。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农业遭到破坏,农民被抽调去炼钢。死亡人数估计在一千五百万至五千万之间。
你写过,他们对党的信仰破灭了。
是的。我小时候,有一天我父亲表情痛苦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是因为人们在挨饿才革命的。”
这就是他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之一。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党制造了饥荒,他彻底崩溃了。事实上,他还给毛写过信。但在四川省省长——我们当时住在四川——的劝说下,他最终撤回了这封信。但这件事一直压在他心头。
你亲眼看到过饥荒的景象,对吗?虽然因为你父亲是党内官员,你们一家在物资上相对被保护。但我记得你说过,有个女孩曾在街上从你手里抢走食物?
是的。有一天我去上小学,正啃着一个馒头,一个小孩冲过来,抢走馒头就跑了。那天晚上我跟家里讲起这件事,父亲摸着我的头说:“你很幸运,别的孩子都在挨饿。”
所以我知道。我看到有人被用小车拉到医院。他们不是瘦弱,而是浮肿、透明的。场面非常可怕。
你记得当时的感受吗?这应该是你童年中非常深刻的记忆。
我当时年纪很小,大概七岁,看到了这些情景,但不明白它们意味着什么。
后来,到了“文革”,父亲开始说出自己的想法,回忆他在大饥荒时期的感受,我就完全理解了他。我觉得,他一生都被失望和幻灭所困扰——他对共产党原本抱有的信念被彻底打破了。
但你父母当时在家里并不质疑毛。这种对话并不存在,是吗?
几乎没人敢质疑毛,特别是在孩子面前。因为孩子可能会说漏嘴,那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灾难。
而且,很多人会想:把孩子培养成异见者有什么意义?只会毁掉他们的一生。所以,即使有人内心有所保留,也不会说出口。
1960年代,“文革”达到高潮时,你的父母被分别送往中国不同地方的劳改营。你和一些兄弟姐妹也被送走。能描述一下那段时期吗?
1966年,我14岁,我的人生彻底改变。我的学校,是中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被变成一个恐怖的地方。我看到一些学生,主要是男生,把校园各处的雕像砸毁。还有一些刻着儒家教义的巨大石碑,被用卡车拉倒,因为太大了。我的学校被毁,我亲眼看到暴力和种种暴行。
那时你会和谁谈论这些发生的事?
老实说,那时候你听到到处有人因为稍微有些不合要求的想法而被批斗,所以没人敢开口。
197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毛去世了。不久后,他的妻子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失势,显然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你还记得当时是不是觉得,终于能释放自己的情绪了?
在我内心深处,我早就开始觉得自己生活的社会是地狱。
我16岁生日那天,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像样的诗。当时我父母被关押,我祖母在隔壁痛哭,因为母亲遭受了虐待。我心里想着:如果这就是中国告诉我们的“天堂”,那地狱又是什么?
就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厌恶这个社会。但当然,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而且那时我也没有质疑毛。我从小被灌输,把毛当作神。他是绝对不能被质疑、甚至不能随便提起的。直到1976年,我才突然意识到,毛才是所有恐怖与苦难的根源。在那之前,我责怪他妻子,责怪红卫兵里的“害群之马”,却没有责怪他。
从我开始厌恶这一切,到真正开始质疑毛,中间隔了很长时间。
这就是洗脑的力量。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无法和任何人交流,也没有任何信息来源,只能在脑子里自己琢磨,这过程非常艰难。

我在想,你是不是被洗脑的时间甚至比你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久?你在新书中提到,写《鸿》的时候,你母亲给过你一个忠告。她说,不要试图写一本历史书,要保持个人化——因为你受到的灌输仍在影响你。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因为那是80年代,你那时已经了解了很多,但你母亲仍担心你因成长经历而依然被洗脑。
我母亲很有智慧,我百分之百同意她说的。在《鸿》中,我尽量压缩历史背景的篇幅。十二年后,我和乔恩完成了毛的传记,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恐慌,因为那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太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我能把故事推进到你来到伦敦那段时间吗?你是最早一批来到英国的中国学生。你曾形容那种感觉像是登上火星。
是的,真的就像登上火星,一切都不同。我离开的那个中国,完全与世界隔绝。我只读过几本翻译过来的当代西方书籍,只看过一部电影——《音乐之声》。
我们当时在伦敦的样子很特别,穿着中山装,不能独自外出,只能集体行动。生活实在太令人兴奋了,一切都是全新的。
那个时期,虽然人在英国,我依然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生活仍然受到中国大使馆的管控。
第一年,我们确实受到大使馆的控制。但那一年我过得非常兴奋,因为我一直在想办法出门,一个人偷偷溜出去。有一次让我们写作文,我说我要写煤气灶。其实我对做饭一点都不感兴趣,但要写煤气灶,我就必须去科学博物馆查资料。结果,没有一个中国同学愿意陪我去。
你在《飞吧,鸿》一书中,写的就是你人生中这一段经历。你怎么看待毛之后的接班人邓小平?他的改革让你有机会出国留学,但他也是在位时下令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人。
我在中国时,他曾是我心中的英雄。我们家跟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妹妹是邻居,所以我们了解他们家。
但现在我的感受很复杂。他确实是中国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如果没有他,毛死后中国可能变成另一个朝鲜。但他决定不否定毛,中国仍是一个压制性的社会,之后也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他留下的这种政治遗产,也让中国今天有可能再次倒退回毛时代,那些可怕的旧日时光。
你怎么看今天的中国?
我当然充满忧虑,非常悲伤。我从没想过会变成这样。我从没想过一个亲历过苦难的人,会愿意让国家和人民重蹈覆辙。但生活就是这样吧。
你说的是习近平?他只比你小一岁,也经历过“文革”。
是的。他父亲当年遭到残酷批斗,他肯定见过类似的恐怖景象。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对那些苦难一笑置之……我真的没想到。
让我感到一点安慰的是,这扇门已经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开放对他本人也有利,因为中国要赚钱,他需要资金来支撑自己的全球野心。
他无法像毛那样,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而有了这个现实,他就无法制造出毛当年那种恐怖气氛。
你看到北京的那场大阅兵——习近平站在中间,一边是金正恩,一边是普京——你看到这样的画面,会有什么感受?
我感到反感。我本来就不喜欢那种阅兵。在朝鲜搞,在俄罗斯也搞。那种正步走,和二战前及期间的德国军队联系在一起。
我非常担忧中国可能会掌控世界。如果真那样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别人又能逃到哪里?
现在的一些局势,比如印度与中国关系更近,部分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舞台上的政策推动。以你的人生阅历,当你看到美国,比如对大学的打击,你是什么感受?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失望,不知从何说起。我不喜欢那种风格,那种自夸。那些价值观,和我曾经认同的西方价值观差得太远。
所以,我只能用“沮丧”来形容我的感受。但美国和西方仍有很多聪明人,我不相信情况会一直这样下去。
某种意义上,你是家里最幸运的那个,有机会在西方生活。你母亲为你插上了翅膀,这也是这本书叫《飞吧,鸿》的原因。但现在的你,却在感到失望,觉得祖国在倒退,而美国也并不是你曾经以为的样子。
但我想,从根本上讲,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如果你陷入悲观,那就等于死了。
我不相信毛主义——不论以什么形式——最终会战胜西方民主。我知道西方民主也正面临各种问题,这种“准毛主义”只是其中之一。但我相信民主,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很多有才华、有道德、有原则的人都能有机会成长。
我想回到你的写作,说一点它对我的意义。你是第一个让我意识到,写普通人的生活同样有意义的人。我后来写了自己的家族故事,如果不是你,我可能不会去写。
啊,那太好了。对我来说,人类的故事最有意思,也是我最想写的。
你说过这本新书是献给你母亲的。她现在94岁了。你已经有段时间没能见她了,她还好吗?
她还撑着。有时候我们能交流,有时候不能。我们用视频通话,所以我会打给她的护理员。能看到她,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安慰。
我欠母亲很多。是她让我有机会来到西方,让我能写作。更重要的是,我成为今天的我,也因为她。是她教会我怎样成为一个人。
你们能交流时,会聊些什么?会谈当下发生的事情吗?
不会。我母亲现在已经过了能讨论这些事的阶段。而且,就算她还能听懂,我也不能在护理员面前说任何敏感话题。
很多年里,我都在努力争取签证,每年都要想办法回去见她。但到了2018年,我意识到,我可能还能回去,但出不来了。那时候我就不再回去了。
母亲理解这一切——我们之间不需要明说,只凭相互的理解。我也无法在她的护理员面前谈这些事,因为我担心她会害怕离开,或者更糟,会虐待我母亲。天知道。所以,生活就是如此。
你的人生经历过许多复杂的时刻,我想提一个你在新书中提到的事件。2005年,你在伦敦出版了毛的传记后,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有一天半夜你发现阳台上的植物全被砍光,连叶子和枝干都不见了。
是的,这件事非常令人不安。我当时倒也没慌乱。到了那时候,经历了那么多极端和灾难性的事情,我反而比平时冷静。但我想,潜意识里一定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件事我从未告诉过我母亲。
阳台是悬空的,只有通过屋子里才能到达,但屋里什么都没有被动过,门锁、窗户都没开。
你当时认为这是来自中国的警告?
我猜是吧。那让我想起《教父》里的情节——对那个不合作的人,黑手党在他睡觉时把他最爱的马的头放在他床上。那是一个警告:我们能找到你。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是类似的、温和一些的警告。
不过,在写毛传记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我当时下了决心,不让这些事影响我,把那些担忧都压到心底。
这次是周末专访,我想知道你平时的周末是怎样的?你是如何保持和中国的联系的?
我和我丈夫现在都不工作了——年纪大了。周末是写作的好时候。办公室不开门,我也不会收到邮件,没有行政事务需要处理。
我的家几乎完全以中国风格布置,到处都是中国的雕塑和绘画。我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因为我小时候亲眼看到中国文化被毁。小时候我曾爬过的铜兽,被送进高炉炼钢。我看到我的学校被毁,那些我热爱的东西都被摧毁了。所以我对中国文化留下的可见痕迹有种深切的情感。
还会有另一本《鸿》吗?你觉得十年后你还会写关于中国的书吗?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不会再有另一本《鸿》了,因为很明显,我母亲现在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飞吧,鸿》的构想,其实是我在2023年才萌生的。所以我们就走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