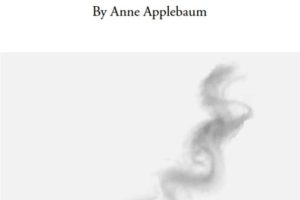盖尔·贝克曼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最新著作是《 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他在文章中旨出,特朗普并非第一个无视外交政策中道义作用的美国领导人,但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以往所有人。

在密室中,已故的亨利·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人权的轻视。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73年3月1日与他的上司、尼克松总统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与其他大量内容一样,被尼克松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设备记录了下来。
当时他们刚刚送走以色列总理梅厄,随后随意地谈起她访问白宫期间提到的一个问题:美国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帮助苏联犹太人——这一群体在国内受到迫害,还被禁止离境。
“让犹太人从苏联移民出去,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国务卿基辛格说。“即使他们在苏联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这也不关美国的事。也许是人道主义的问题。”
他说了声“也许”。
这番话出自一个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在美国寻得庇护的犹太人之口,格外冷酷。但这也正是基辛格风格的典型体现,他那种现实政治哲学的最纯粹体现: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务实必须占据上风,道德、美国那种“传教士式的热情”——他在著作《外交》中轻蔑地称之为如此——都没有立足之地。
也许没有哪个美国外交官,像基辛格那样鄙视理想主义在人权外交中的角色——那些人权活动者和民主鼓吹者的“干预”。直到今天,这种局面才发生转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前100天内,特朗普不仅摆脱了基辛格当年不得不应对的那些碍事的“好人”,甚至只靠几次猛烈出击,就彻底将他们扫地出门。
这种变化,是基辛格曾梦寐以求的,如今却令人震惊地成为现实。
通过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以及清除国务院中处理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办公室,特朗普几乎在一夜之间摧毁了整个曾致力于捍卫基本(曾被认为是美国核心)价值的政府体系。
成立于1941年的自由之家,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组织之一,现在将结束80%的项目。
国家民主研究所和国际共和研究所这两个政府资助的机构,过去在海外监督选举并支持反腐努力,如今已遭“DOGE”的锯刀砍伐——这两个机构已让三分之二的员工停薪留职,并正在全球各地关闭办公室。
第三个组织,全国民主基金会,目前正在为保住经费而与国会搏斗。
还有一道行政命令,直接关闭了美国全球媒体署,这个机构运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并向伊朗、委内瑞拉、朝鲜等国家进行广播。这些电波每周传送到100多个国家的4.2亿人耳中。如今全都没了。
特朗普政府甚至还撤销了威尔逊中心,这个外交政策智库的思想可能和名字太过密切——威尔逊总统以倡导“道义外交”而著称。
基辛格会感到高兴吗?
他确实对人权持负面态度,但那是因为人权是他实现首要目标——维护世界稳定、防止核战争——的障碍。就他的道德观而言,他认为只要能在主要国家之间维持一种以相互利益交织为基础的力量平衡,就可以遏制地缘政治的混乱与不可预测性。如果几个苏联犹太人不得不作为附带牺牲走进毒气室,那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以换取避免与苏联摊牌、引发全球毁灭的更大利益。
虽然这代表了一种为了更高目标而进行的交易主义——哪怕道德上令人不齿,但现在的特朗普,则变成了彻底的交易。特朗普似乎扫除道德考量,不是因为妨碍了他设想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考量根本毫无价值——正如他的国务卿卢比奥所说,那些是“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
这并不是说过去的美国总统本质上更理想主义(虽然吉米·卡特可能是),他们只是找到了利用人权和民主促进作为宣传工具,以实现全球目标的方法——例如里根将共产主义描绘为无神论和不道德体制,乔治·W·布什把伊拉克战争包装成推动中东民主的大策略。
特朗普根本无意使用这些理念。他眼中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美国必须表现出自己是最强的那一个。
就这样,不服来干。
我请教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作者杰雷米·苏里,让他从基辛格的角度想象这过去的100天。
“他会高兴看到力量优先于理念,”苏里说。“他长期批评美国沉迷于威尔逊式的执念,把软性元素、理想主义元素置于力量元素之上。”
基辛格还会欣赏特朗普对强国的重视,以及对国际组织如欧盟和联合国的轻蔑态度,苏里说,这些机构在基辛格眼中“最多只能算个麻烦”。
基辛格也有自己的“特朗普式时刻”,在那种情况下,他在几乎不顾后果的情况下动用了美国的力量。智利的秘密干预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1970年,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大选,基辛格担心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散,他没有选择建立某种平衡,而是决定立刻消灭这个威胁。
他据说曾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因为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
在加拿大最近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以大约44%的得票率获胜,人们甚至不难想象特朗普说出类似的话。
基辛格在智利促成的军事政变,引发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残暴统治,这不仅让整个地区更加不稳定,还破坏了他追求全球稳定的更大战略目标。
而他在另一部分更为有效——更持久、更不“特朗普化”的战略举措中,确实推动了全球力量格局的“系统性转变”,正如苏里所说:与苏联实现缓和(不管那些犹太人的命运),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哪怕数千万毛时代的受害者被抛在脑后)。这些行动同样没有考虑道德因素,但至少有清晰的战略意图,旨在实现更多的安全与稳定。
是否值得做出这样的交换,是基辛格的遗产留给我们的疑问。
他绝不会预见一个美国外交政策中“传教士精神”完全消失的世界。理想主义者曾是基辛格的对立面,即使他们称他为“战争罪犯”,就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那样。但基辛格知道,他们一直是制衡力量,是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传统力量。
如果这股力量不再存在,一个更冷酷、更残忍、更自私的现实政治版本就此上台,这意味着什么?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一篇关于国务院新变化的报道中,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根据一份备忘录,员工被要求“精简”国务院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使其与“近期发布的行政命令”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份备忘录解释说,报告应删除诸如监狱虐待、政府腐败和无正当程序拘押异见人士等内容。报告中只能保留国会法律要求的最基本内容。
在有关萨尔瓦多的报告中,其监狱系统已成为被美国驱逐的移民的“垃圾场”,但报告中将不再有关于这些监狱条件的细节。而关于匈牙利——特朗普在那里的盟友是强人奥尔班——备忘录显示,“政府腐败”这一部分将被删除。
即使在过去,美国无视自己的理想,或者只在表面上提及它们,或者有像基辛格这样的领导人刻意绕过它们,这个国家仍然以暴政行为的记录者自居。
如果你是异见者或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你曾至少能安慰自己: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中,有人正在撰写一份报告,有可能记录你所经历的歧视或屠杀。美国曾给予人们发声的机会——一条热线,另一端有人愿意倾听。
但现在,特朗普正将这条热线彻底切断。已经没有人接听这通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