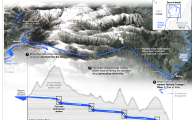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的中国茶馆栏目。

杰罗姆·科恩无法保持沉默。
1972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受邀与周恩来共进晚餐——对外国人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
科恩没有局限于寒暄,而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一系列自己关注的问题。他敦促周恩来释放他的一位老同学,这位同学二十年前因间谍罪入狱;还呼吁中国向美国派遣学生。
作为法律学者,他甚至建议中国加入国际法院。
当时周恩来对这些提议没什么反应,时机尚早。最引起笑声的就是中国加入国际法院的想法。对正在经历文革的共产党政府来说,参与“资产阶级法律机构”根本不可思议。
但对科恩而言,这很自然:中国是大国,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与这样的重要对话者会面时,他无法放弃表达对正义的看法,即便这些倾向最终让他失去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9月22日去世的科恩享年95岁,他远不止是一名律师。在一段极为多元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成为中美深入交往价值的化身,也体现了这种交往所伴随的挫折。
他的经历既是对西方“逢中必反”的鹰派态度的回应,也是对“盲目乐观”派的一种矫正。
科恩事业的跨度和持久性赋予他独特的视角。
他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兴趣,部分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红色恐慌”。当时中国问题专家凋零,美国官员开始重建队伍。这对科恩来说反而成为契机,他放弃了前途光明但传统的美国法律学术道路,转而投身中国法律研究,并最终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者。
他通过在香港对大陆难民的广泛访谈,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刑法著作。
就在毛发动文革后不久,他完成了这本书。这种时机使他对中国的发展更有耐心,自称因此“更有准备”去保持一种长期视角,即使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时亦如此。
面对近年来习近平的威权复兴,他依然保持乐观。今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统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政治钟摆终将再次摆向温和体制。”
在某种意义上,科恩还是中西交流的架构师之一——这一项目如今正承受巨大压力。
现代中美关系常追溯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基。但在更早几年,科恩和少数学者就起草过一份机密备忘录,论证为何需要接触以及如何实现。
随后他更进一步,将交流付诸实践,离开学术界成为在中国执业的首批外国律师之一。
他的客户名单包括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巨头。但科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在处理企业事务的同时,也积极为人权奔走。
他最早是为身边熟人出头——包括他曾在周恩来面前提及的大学同学约翰·T·唐尼。80年代,他关注哈佛校友吕秀莲的获释,当时她因台湾威权政权而入狱。
译注:约翰·T·唐尼(John T. Downey)在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情报员。1952年,他奉命与另一名CIA特工进行一项秘密任务,驾驶飞机在中国东北境内接应并营救潜伏人员。但行动失败,他们的飞机在辽宁被击落。唐尼与另一名特工理查德·费克图(Richard Fecteau)被捕。
天安门事件后,科恩对中国的压制愈发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来自一位专家之口,分量更重。
他重返学界,在纽约大学接待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律师与维权人士,并介入个案——最著名的是帮助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入读纽约大学(尽管陈很快与NYU闹翻)。
近年来,他谴责中共在香港、新疆以及对独立律师的打压。2020年因批评习近平而被捕的中国教授许章润,在科恩去世后写下悼文:“我的精神家族失去了一员。”
科恩的一生引出了一个问题:接触政策是否失败,甚至是错误?
他本人对此常常反思,担心自己和其他人是否帮助造就了一个利用现代法律工具进行控制的共产党。
科恩的回答之一是,这种担忧严重缺乏历史感。70年代末,中国刚走出文革,需要法律来避免重蹈混乱。
把中国拉近西方,也加剧了俄罗斯的孤立,推动冷战终结。他说,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大幅改善——当然不是所有人。
科恩的另一个回答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认为,不排除有一天,“一个越来越受教育、更加成熟的公众,可能会要求一个更开放、管控更少、个人自由保护更强的社会”。
今天,这个前景似乎令人心碎地遥远。但科恩在批评中国的演讲中,喜欢以一首台湾80年代流行歌曲的标题作结:“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