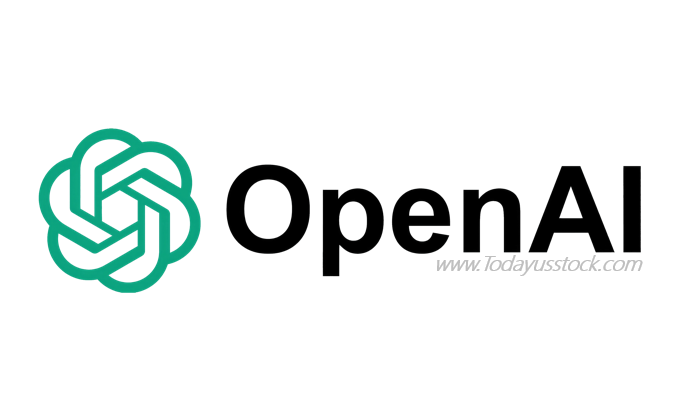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35岁的纽约人斯蒂芬·弗格森今年6月走进一个会议室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来自中国顶尖科研机构的50人,正在等待听他讲述在这座中国南方城市工作的经历。

弗格森在2023年被招聘为生物学研究员,尽管此前他只来过中国一次。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团想知道如何提升科研环境至一流水平。
“他们想听一个来自美国的普通人讲讲经验,这对我来说象征着更大的意义,”他说,“我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环境中,这里在成长,在吸引人才。他们让人很容易说,同意。”
弗格森并不是唯一一个选择“同意”的美国科学家。
过去十年间,大批学者横渡太平洋赴华工作,其中很多人有中国背景,被北京全力打造科研强国的愿景吸引。
而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更加快了这个进程。特朗普政府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科研经费,取消了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科研资助,撤销国际学生签证,并提高高技能H-1B签证的费用。
科研经费的削减,加上美国对华裔科学家的审查加剧,进一步推动了北京吸引顶尖人才的努力,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科研中心的地位。
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学术数据库和公开资料数据发现,仅今年上半年,就有约50位具有终身教职的华裔学者从美国大学离职前往中国。自2011年以来,这一数字已超过850人。
普林斯顿的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离开的学者从事理工科研究,工程和生命科学领域的转变最为显著。
仅今年,就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高级生物学家、哈佛大学的世界级统计学家,以及曾在美国能源部工作的清洁能源学者加入中国高校。
本周,杭州的西湖大学宣布,前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弗兰克化学教授林文彬加入该校。
科学人才的迁移,将对全球科研生态系统及日益激烈的中美科技竞争产生重大影响。两国科学家指出,美国的竞争优势正被蚕食,下一代疫苗或人工智能模型更可能在中国诞生。
“美国越来越怀疑科学,无论是气候、健康还是其他领域,”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中国科技专家吉米·古德里奇说,“而在中国,科学正被视为推动国家走向未来的关键解决方案。”
这种人才流动也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宣传胜利,帮助习近平实现到2035年将中国建成科技强国的愿景。
“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掌握了世界的未来,”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家赵永升说。
北京在人才引进方面投入巨大。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是中央科研资金主要来源机构,正将其每年约800亿美元预算中的越来越多份额用于人才计划。各省、市和高校也纷纷推出相关支持措施。
上个月,北京还推出了新的K类签证,吸引年轻外国理工科人才。不过,这一签证引发了争议,特别是在年轻毕业生中,他们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市场中面临激烈竞争,不希望再多出外国竞争者。
尽管美国依然在全球科研领域拥有诸多优势,仍是许多科学家向往的地方,但中国正在迅速追赶。
20年前,美国在研发上的支出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但到2023年,中国几乎追平。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数据,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在研发上的总支出达到9560亿美元,仅略高于中国的9170亿美元。
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资金是否能转化为科研成果,这些归国或赴华科学家是否能在政治环境截然不同的中国取得突破。
北京长期以来就试图吸引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于中国的研究人员。比如“千人计划”,就是一个高调的国家项目,旨在通过财政激励吸引顶尖学者回国。
爱国情怀和对推动中国科研发展的愿望,是一些人回国的重要动力。例如,哈佛大学统计学家、华裔学者刘军今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觉得我在这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提升中国统计研究的水平。”
但如今一些人觉得,是美国在“推”走科学家。今年5月,哈佛医学院免疫学家乔纳森·卡根参加苏州的一个学术会议时,不断有中国科学家对他说:“我们希望特朗普一直当总统,因为这对中国科研是最好的事。”
对于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来说,这种压力尤其明显。2018年,美国政府启动“中国行动计划”,调查与北京有联系的研究人员。
这个项目导致大批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大学,他们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尽管拜登政府已在2022年取消了这个计划,但影响依然存在。
离开的不只是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哈佛大学纳米科学家查尔斯·利伯是“中国行动计划”最知名的调查对象之一,2021年因伪造税务申报和隐瞒海外资金而被定罪。
今年4月,他成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全职教员,这是清华大学专注理工科研究的分校。
利伯在欢迎仪式上,表示期待将“雄心勃勃的科研梦想变为现实”。
就连长期未受科研经费冲击或政治变化影响的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
被誉为“数学莫扎特”的UCLA数学家陶哲轩,最近有2600万美元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被暂停。虽然后来恢复,但他表示,中国高校已经主动与他联系,试图吸引他加盟。
在美国生活30多年后,陶哲轩此前从未考虑离开美国。但他表示,当前对高等教育的攻击迫使他重新审视美国能否继续保持科研领先地位。“我现在什么都不确定了,”他说。
在中国科研版图中,没有哪个城市比深圳更核心。
这个从渔村发展为科技都市的中国南方城市,吸引了全球研究人员。他们被先进的科研设施、不断扩展的大学校园、丰富的资源,以及与华为等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的地理接近所吸引。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院长欧阳征在采访中表示,深圳是教育与前沿产业之间的“交汇点”,是一台“新的产业引擎”。
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正是为这台引擎而设。目标在未来十年将教职人员数量增加三倍,鼓励大胆创新的教学模式,更像一所美国大学,吸引了大量有海外经历的学者。
约八成教员有海外教学或研究经历。欧阳本人就是如此,他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多年后,于2017年回国。
前来深圳的,远不止学术界明星。新兴研究人员也在这里扎根。
比如38岁的亚历克斯·刘,出生于中国,在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获得蚊子研究博士学位。他在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奥本大学的橄榄球纪念品。
“我在美国真的没找到太多机会,”他说。
2023年,也就是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前,刘加入了由地方政府支持的深圳湾实验室,这是一家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也因此能更接近家人。
目前,他领导一个超过10人的团队,研究蚊子生物学和疾病传播,他们的工资部分由深圳市政府资助。
弗格森曾在美国与刘共事,如今是他团队中的博士后。
弗格森说,离开美国前,他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科学的排斥”。现在,他不仅获得了五项除工资外的资助来支持研究和生活开销,其中包括广东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他的收入也高于美国的报价。
中国的科研机构还尽力让国际科学家感受到特殊待遇。
据在华学者和招聘信息透露,外国科学家和回国人才常享有优先获得育儿和教育资源、创业基金等待遇。
尽管有这些优待,对于没有中国背景的外国科学家而言,适应生活和文化仍需时间。
赵永升指出,在美国长期工作的研究人员,可能在中国面临信任缺失或被排斥的处境,“因此他们人数仍然不多,影响力也有限。很多人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后,会感到受限,最终选择离开。”
此外,科学家还要面对中国的政治环境。
“在中国,学者的工作自由受到限制,要服从行政管理,”领导普林斯顿人才流动数据研究团队的社会学教授谢宇说,“中国的大学体系是僵化的。”
最终,在中美两国争夺人才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必须在两国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他们被夹在中间,”谢宇说。